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在抗肿瘤、抗病毒、抗炎等领域,
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展现出陆地生物
难以比拟的潜力。”
7月中旬,山东青岛东海岸的海水浴场遭遇浒苔侵袭,大片绿苔漂浮于海面,散发异味,不少外地游客只能远远看海,不愿靠近。
南极褐藻是浒苔的“远房亲戚”。海水浴场数十公里外的青岛西海岸,青岛国信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制药”)正开展候选药物BG136临床试验,这款候选药物就是由南极褐藻的活性成分研发而来。国信制药副总裁陈阳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该候选药物顺利通过临床试验并上市,或为癌症治疗带来转机。
海洋,可能蕴藏着更多绝症的解药。目前,大多数药物的来源可追溯至陆地生物。海洋覆盖地球71%的表面积,拥有更庞大的基因库,与陆地相比,海洋环境更为极端,生物演化出更多样的活性化合物,是创新药的重要来源。

图/视觉中国
大约60年前,科学家开始将药物研发的目光投向海洋。目前,全球已有40多种海洋药物及衍生产品获得监管部门批准,150多种化合物正处于临床试验或临床前阶段。据估计,至少90%的海洋微生物尚未被发现,这些生物蕴含着巨大的药物开发潜力。
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中国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全国沿海多地正加快相关产业布局,然而,和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由于起步较晚、研发经验不足,在资源获取与成果转化等环节面临更多挑战。
“突破重大疾病治疗的瓶颈”
深海是地球上最严酷的环境之一,这里压力高达110兆帕,温度只有2℃—4℃,常年黑暗,还伴随高盐、缺氧等极端条件。为了在这种环境中生存,深海微生物演化出独特的机制,比如嗜压菌会调整细胞膜的分子结构,分泌的酶在高压下仍具备高效的活性,这在药物合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海洋生物体内的生物活性物质往往结构独特、功能多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药学院院长、海洋药物融创中心主任林厚文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深海环境中生存竞争异常激烈,微生物为争夺有限资源,会产生强效的抗菌、抗病毒甚至对细胞造成损伤的代谢产物,这些产物为新药研发提供了大量候选分子。
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党委副书记、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以下简称“海药院”)执行院长张栋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目前,全球已在海洋生物中发现4万多个化合物,其中大约60%满足“类药五原则”,即具备成为药物的可能性。海洋生物资源占地球生物总量的近九成,而且,重要海洋天然产物的成药潜力是陆生生物的5倍,具备巨大的医药开发空间。
“海洋药物的核心价值在于突破重大疾病治疗的瓶颈。”林厚文介绍,过去五年,全球进入临床阶段的海洋药物中,超过一半用于肿瘤治疗,并且在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和代谢性疾病方面也展现出巨大潜力。
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统计,具有抗肿瘤活性的海洋天然产物约占全部海洋天然产物的1%,在陆地天然产物中,这一比例仅为0.01%。据智研产业研究院统计,2023年中国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规模已增至739亿元。张栋华介绍,海洋产业的15个主要门类中,海洋生物医药是最具潜力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产业增加值增长迅猛,成为一个少有的“国家有需求、地方有动力、科研机构高度关注”的领域。
早在20世纪80年代,海洋药物研究就被正式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中国第一款现代海洋药物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当时,在烟台水产学校工作的管华诗发现,海带提碘后的副产物海藻酸钠,经过改性后表现出良好的溶解性。于是,他想到,能否用它来溶解血栓。这一简单的想法,加上一些偶然与运气,便催生出了藻酸双酯钠(PSS)。在药品相对紧缺的年代,这一药物迅速成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常用药。
管华诗之后历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校长,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基础上,他先后成立了国家海洋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海药院,并在2016年发起“蓝色药库”计划,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研发和海洋生物资源利用。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多份文件提出加快推进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的产业化应用。“蓝色药库”入选2024年全国十大海洋科技研究前沿热点。
目前,全球已上市的近20种海洋创新药物中,有两种由中国自主研发,而仅“蓝色药库”计划就正推进40余个海洋药物项目。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在海洋药物领域的起步时间与国际相差不大,有望像新能源汽车产业一样,在关键技术上“弯道超车”。
资源之困
鲎(hòu)是一种海洋生物,有特殊的蓝色血液,其中的阿米巴样细胞遇到细菌会迅速凝固。由鲎血提取的试剂被广泛用于毒素检测和药物研发。随着数量锐减,鲎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鲎试剂供应也日趋紧张,影响多款药物的临床试验进程。

鲎 图/视觉中国
这是制约海洋药物发展的一个缩影。林厚文介绍,海洋药物研发风险高、投入大、周期长,其中资源获取是首要难点,也是海洋生物医药的特殊卡点。
全球范围内,已上市的海洋药物主要来源于海洋动植物。厦门医学院教授、厦门市海洋药用天然产物重点实验室主任罗联忠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相较于动物,海洋植物的获取和培养更为便利,生物量充足。但藻类的活性化合物种类有限,多用于生物制品领域。
罗联忠介绍,20世纪的海洋药物研发主要集中于海绵、珊瑚和海鞘等海洋动物,它们含有大量结构新颖、多样的化合物,活性突出,成药潜力高,但是存在“三难”问题,即资源捕获难、结构解析难、化合物合成难。为此,科研人员尝试人工养殖和化合物提取,但目前尚无法全面解决药源保障问题。“海洋动物中的许多活性物质,其实是由宿主和其共生微生物协同产生。”罗联忠介绍,海洋微生物的基因资源和化合物种类更加丰富,2000年开始,逐渐成为全球海洋药物资源发现的主力方向。
不过,培养海洋微生物的技术要求更高,即便培养成功,目标化合物也可能处于沉默状态,也就是说,无法获得具有药用价值的成分。林厚文介绍,由于深海到陆地的压力骤变,超过一半的深海微生物会在采样途中死亡,而且,绝大多数的深海微生物无法在传统培养基上生长。例如,深海热液口的微生物,可以在高温、高硫等极端环境中产生、存活,只有模拟其自然生境,才能成功培养并提取其特殊化合物。
2004年,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大洋深海生物资源调查首席科学家邵宗泽创建了中国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管理中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和海洋动植物相比,海洋微生物可以通过发酵、合成等路径进行工业开发,突破生产规模的限制,实现海洋资源到海洋产品的跨越。
邵宗泽介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帮助下,海洋药物的筛选效率大大提高。海药院海洋医药健康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锡明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过去在药物筛选中,通常对海洋天然产物进行疾病盲试,现在借助大数据分析和高通量筛选技术,可以将海洋天然产物的三维结构与疾病靶点数据库进行分子对接,“就像拿着钥匙去开锁,我们正在研发的一款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发现的”。
林厚文认为,要突破海洋药物研发的资源难题,一方面,要依托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加速药物研发,以青岛华大基因为例,其建成的全球首个海洋药物智能创制平台,已实现“采样—筛选—合成”的全流程自动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国产深海采样装备的技术攻关,打破采样技术的瓶颈。
“地球上90%以上的生物宜居空间在深海中,目前国内多家科研机构正在建设海洋微生物库、动植物库和基因库,正是为未来的药物开发打下基础。”张栋华表示。
转化难关
目前,中国已上市的两款海洋创新药,均来源于海洋天然活性物质,属于多糖类化合物。而国际上其他上市海洋药物在化合物类型上更加多样。厦门大学药学院创始院长张晓坤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围绕天然活性物质展开应用研究,是一种较为传统的研发路径。天然来源药物通常成药性较差、作用机制不清、知识产权难保护,还需面临更为严格的审评标准。
现代海洋新药研发更常见的路径是,以活性分子为“钥匙”,寻找对应的作用靶点,再围绕靶点设计新药。张晓坤介绍,“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海洋化合物发现方面,中国处于世界领先”,从化合物类型与靶点分布看,中国进入临床阶段的海洋药物已基本接近国际同期水平,但从数量上看,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能真正转化为新药的仍然很少”。

2024年6月7日,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研究人员在实验室进行研发测试。图/新华
林厚文介绍,和其他药物相比,目前中国海洋药物的研发成功率更低。其背后,是海洋药物产业化能力的不足。
“药物研发历来是万里挑一、九死一生,海洋药物既有新药研发的共性特点,更有其研发独有的困境。”张栋华分析,“国内海洋生物医药的产业化率仅有5%,远低于国外平均30%的水平。”他认为,与其他药物相比,国内海洋药物产业化的特殊难点,在于积累少,还处于一个被观望甚至被忽视的阶段。绝大多数药企更关注药物的适应证和产品布局,很少单独投身早期的海洋药物开发中。例如,某药企以海兔毒素为核心成分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ADC)上市后,主要围绕“ADC 药物” 技术品类宣传,并不会特意强调其海洋药物属性。
在“纺锤形”的创新药投资结构中,有限的资金主要投向从0到1的早期研发项目,以及已较为成熟的候选药物。罗联忠坦言,也就是说,一款海洋药物从先导化合物到临床前的药学研究,即从1到10的阶段,各级科研项目的经费远不足以支撑,而相较于化合物修饰改性这样的工作,科研人员更倾向于聚焦前期的创新发现研究,“因为更具学术创新价值,也更容易发表成果”。
在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药物筛选中心主任杜冠华看来,当前海洋药物的前期探索主要由科研机构承担,非沿海地区的药企远离海洋资源,对海洋药物关注度不高;沿海企业也多聚焦中后期开发。“这种分工并无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突破海洋药物产业化瓶颈的关键,在于科研团队要有明确方向和稳定投入,让药企关注到有潜力的候选药物。
多位受访者表示,目前已上市的海洋药物更多依赖于院士团队和既有研发经验,要推动更多海洋药物上市,还需撬动更多资源。2013年7月,中国海洋大学等单位联合创办了海药院。这一机构类似于“转化器”,一端连接海洋资源,另一端对接海洋药物的产出,但能推动多少新药上市,取决于“转化器”的机制和效率。
为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海药院聚焦“半成熟成果”的熟化和产业化,将学校科研人员筛选获得的具有成药潜力的先导化合物推进至工程化阶段,并通过设立子公司、发起联合创新中心、共建产业转化基地等方式,推动与青岛本地产业资本的对接与落地。
如何激励科研人员参与药物转化?海药院院长助理李全才负责研究院的产业化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海药院设有多种激励政策,在研发过程中每完成一个里程碑节点,科研团队都会获得阶段性激励。“激励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科研人员收获了专业领域中的个人成长。”他还表示,一位高校教师如果能主导一项新药研发并获得临床批件,意味着他获得了一项突出的综合性成果。
企业也是海洋药物研发的重要力量。张晓坤团队目前有两款来源于海洋的化合物进入临床Ⅰ期试验,都是全程由药企主导研发。抗肿瘤海洋药物BG136是“蓝色药库”的重点项目之一。
“需更高层级的机构统筹协调”
目前,青岛、宁波、上海、厦门、珠海和三亚等多地都建立了海洋药物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园,多位受访专家指出,这些沿海地区的自发行为,存在着资源配置重复的问题。

青岛国信制药有限公司的海洋药物中试基地 图/受访者提供
多位受访者提到,海洋药物很难迅速产出可见的转化成果,或导致地方缺乏持续支持的动力。面对研发经费的紧张,海药院同时布局了海洋医疗器械、保健品和食品的资源开发,从服务企业委托的项目开始,依靠新药转化带来的收益,才能持续研发。
区域之间资源流通不畅,也是海洋药物研发的一大障碍。科研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仍然有限,这背后关键在于利益分配机制尚未理顺,缺乏完全公益性的数据和资源平台。“如果能建立类似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美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那样的国家级基因数据中心和微生物菌株资源中心,推动资源标准化管理与开放共享,将大大提升海洋药物研发效率。”陈阳生也提到,由于前期科研经费多来自地方,当国信制药推动山东省外的候选药物转化时,常常面临更大的行政和政策壁垒。
“不同机构间交流受限在科学界并不罕见,但在海洋药物这一仍处于‘跑马圈地’阶段的新兴领域,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杜冠华认为,海洋药物研发的早期阶段,各地自发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复投入,形成各自特色与协同优势,但要真正推动一批海洋新药落地,仍需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与协调机制。
杜冠华曾参与“863计划”和“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他介绍,过去数百亿元的专项资金推动了中国创新药研发体系的建立,但海洋药物始终未被单独列为重点方向。他建议,未来应设立国家级海洋药物产业发展创新中心,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如果政策机制完善,就能吸引更多内陆企业和科研机构下海,参与海洋药物开发。”
但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张栋华认为,海洋药物的研发与上市涉及科技、海洋、卫健、药监、医保等多个部门,“九龙治水往往治不好水,单靠某一部门又难以推动系统性突破,这需要一个更高层级的机构统筹协调”。林厚文也认为,海洋药物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不仅要跨越技术和产业门槛,还需迈过医保支付等关口,与其他药物同台竞争。
罗联忠认为,全球生物医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源头性大科学计划的持续推动,“海洋药物要实现突破,同样需要持续性的国家级大科学计划的稳定支持”。
发于2025.9.1总第120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深海基因,激活“蓝色药库”
记者:孙厚铭(sunhouming1@163.com)
责任编辑:陈琰 SN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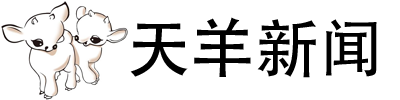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